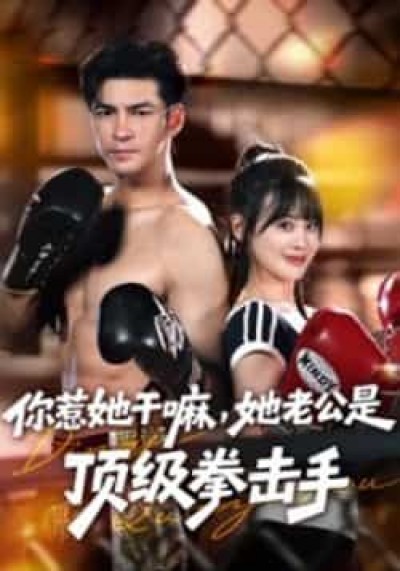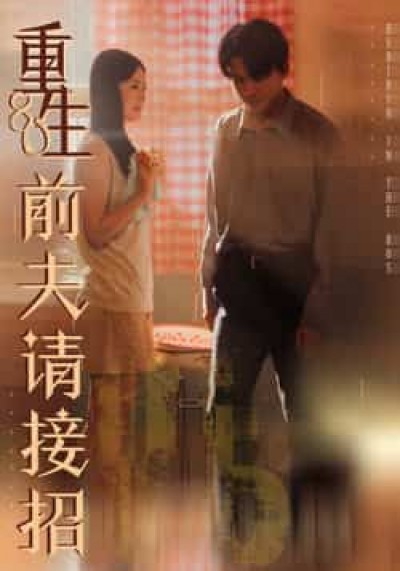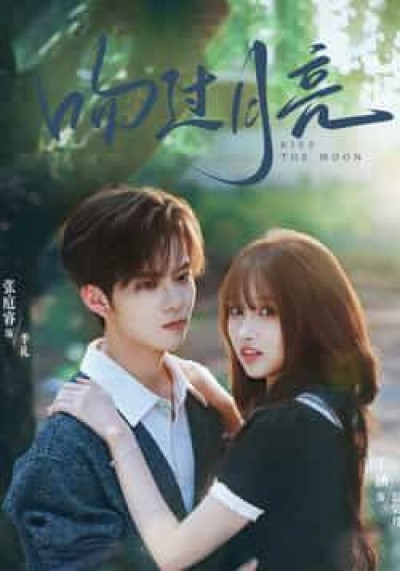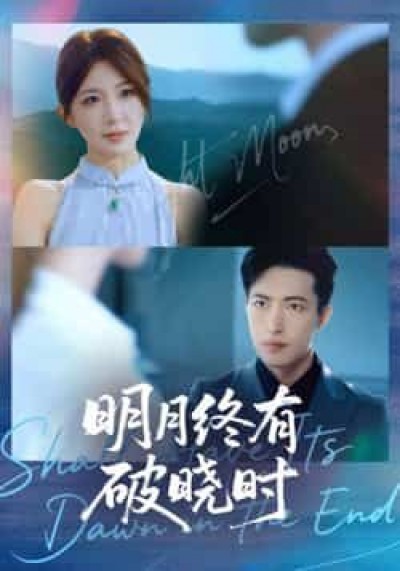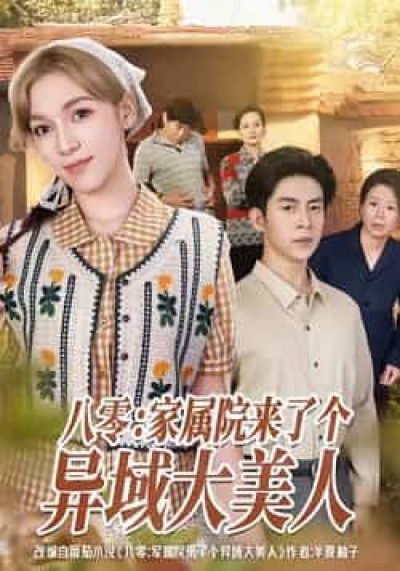1980年代的春风裹着棉纺厂的油墨味,吹过返城知青周子豪肩头的帆布包,他原以为要在织布机的轰鸣里重复父辈的轨迹,却在某个雨夜误入厂区舞厅——当藏在怀里的现代街舞撞上迪斯科的鼓点,他笨拙却炽热的旋转,瞬间点燃了沉寂的角落,“周子豪”三个字成了年轻人嘴里的“舞王”符号。
纺织女工林晓梅第一次见他,是在他踩着滑板撞翻晾晒的蓝布工装时,这个总穿喇叭裤、头发用发胶抓得高高的小伙子,在她眼里是“不务正业”的异类,可当舞厅灯光落在他飞扬的衣角,听见他改编的迪斯科里藏着的对自由的渴望,冰封的心墙悄然裂了缝,从“跳舞能当饭吃”的争吵,到偷偷跟着他练舞步的笨拙模仿,两个被时代裹挟的年轻人,在织布机的梭声与鼓点的间隙里,找到了彼此的频率。
他们用攒了半年的工资盘下街角废弃仓库,挂上“青春舞厅”的木牌,当厂长抻着脖子骂“伤风败俗”,当林晓梅母亲哭着说“姑娘家跳什么舞”,他们带着一帮同样热血的伙伴,用舞步踏碎偏见——在喇叭裤与的确良的碰撞中,在《霍元甲》与《路灯下的小姑娘》的切换里,舞厅成了八零年代的青春据点,50集的复古光影里,真正的“舞王”从不是聚光灯下的王者,而是敢带着时代起舞的人,每一个旋转都是写给热血年代的青春情书。